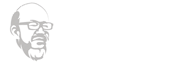《人类的没落》前 言
这是一个摘编于我的其他著作之附录文章的单行本。
其中《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一文,原本主要是为了回应《物演通论》的部分读者,动辄提出如下问题:你所搞的那一套哲学体系何用之有?把世“道”说得如此不堪,总该拿出某种挽狂澜于既倒的方略吧?或者,那怕是一条逃路也罢?为此,我勉强写下此文,结果好像愈发证明了哲学的无用,以及前途之渺茫。
《哲学史与〈物演通论〉述略》一文,是我的几位好友多年来一直催促我写一本哲学史,而我又慵懒怠惰的无可救药,情急之下,草成简章,以慰友人期待之笔墨。在我,窃以为哲学史之不可写,还有两重原因:一则,有独到之见者,如黑格尔或罗素之辈,作哲学史如作自家思想之余绪,笔锋所至,“史”已不史;二则,无自主之见者,如书铺里充斥的附会文本,编者恐怕自己都未曾真正读懂过哲学,还谈何史论?我既不肯委身于后流,又恐怕逃不出前类的窠臼,于是干脆直接写明本人之观念与哲学史的纠葛,且笔下寥寥,未敢烦言,以免误人。
至于那篇看似论文的《递弱演化的自然律纲要》,其实一开始就没有循着一般论文的格式落墨,起初是想将《物演通论》中深入论证的递弱代偿原理,归整成一篇可以译成外文的简明提纲,结果我力不逮,借力也终于无成,不伦不类的东西,加上不合时宜的观点,投稿于多家刊物自然只能碰一鼻子灰回来,而自养的畸形儿,总不忍心自己下手淹了它,想想刚好可以附在《知鱼之乐》后面作为散乱随笔的纲领充数,于是,它就这样摇摇晃晃地苟活下来了。现在拿来补在这个单行本里,又起到阐述原理的轴心作用,也就顾不得它的丑陋难看了。
惟有《人体哲理:生物畸变与进化衰变的极致》一文,可以说是专为此书而著,它原先只是我替西安交大准备的一个系列讲座提纲,从未将它看作是具有成书价值的东西,不料出版社方面对于这本小册子的装帧单薄深表忧虑,认为它的体量不足很有可能严重影响其市场营销,无奈之余,只好将那个讲演提纲用最简略的文字填充起来,以渡饥荒。不过,写完后再一看,觉得它也不全是一个“打肿充胖”的无聊角色,其中既体现着我的哲学观对人体的别样透视,也成为本书中唯一一篇稍具实用价值的现代保健杂谈,回想当年老聃诺大的宇宙观竟被后世之道教庸俗化成了一系列“保真养生”的道行,谁还敢断言这篇奇文将来不是我所有文字中唯一可供传世的“真经”?
最后,为《〈物演通论〉导读》说几句话,它是我十余年前撰草《物演通论》之初稿时的一篇收笔之作,也是初版《物演通论》时未被采用的一纸弃文。二版时编成附录面世,已时隔五载;今日再看,更显老朽沧桑。然而唯有它还能透露出一丝昔时隐居于山野世外、专注于纯粹哲思的虚静和飘逸,对比之下,前列那几篇应时媚世的文章,简直就是不堪卒读的硌牙残渣了。放在里面,作为参照,以便未览该书的读者略微体验或沾染一丁点儿超绝尘寰的仙气。
总而言之,将它们汇集在一起,大约刚好可以用最少的阅读量,以窥得我的哲学系统之全豹,但也毕竟只是其花色斑驳的皮毛而已。
以上算是我对此书的构成做了一番简单的交代。
下面谈谈书名问题。一望而知,这个骇人的书名只不过是我的一篇附录文章的半截题目而已,但我深心里也并非全然没有从另一个角度回应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意图。
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一战前即开始着手写作《西方的没落》,发表时正值一战结束,其对西方文明必趋衰微的预言,恰好与空前惨烈的西方列强之自杀式对决相印证,结果在欧洲引起的震撼连斯宾格勒本人也颇感意外。实际上,斯氏所用的写作方法完全是粗浅的生物生长形态对照或曰“外部观相式”描述,虽然后来被溢美为“文化形态学”或“历史形态学”的开山之作,但在当时被人讥评为“历史的占卜术”却不能不说是中肯之至。这个事件仅仅表明,欧洲人对“西方中心论”是何等的执迷、以及包括斯式本人对“文化与文明发生学的内在机制”何其缺乏了解。
不过,无须斯宾格勒用他那肤浅而凌乱的生花之笔来证明,“西方的没落”早已被资本主义的汗渍和世界大战的血污明晃晃地写在了一片狼藉的欧洲大地上。
有趣的是,当时的中国适逢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狂飙骤起之际,“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文化西化运动”的别称,而所谓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也没见得怎样触动了“帝国”(实乃“宪政”)主义列强的毫毛或“封建”(实乃“君主”)专制主义的筋骨,它所抡起的大锤反倒进一步只把东方别具的传统文化砸了个粉碎。说来好笑,那时推崇西学与西风的知识界也将《西方的没落》视为异端和芒刺,某些立于潮头的学者还唯恐它给正处在“启蒙”(其实是“洗脑”或“换魂”)中的国人带来负面影响,建议最好不要译介。
此时此刻,东西方文化第一次展现出了某种奇怪的默契:原本极端稳定的一方由于骤临冲击,而决定无条件地把自身移位到那个特别动荡且行将衰丧的一方之最高危的滑坡顶端上去。自此以降,我们跳出了油锅,又堕入了火坑,而且只剩下了一条出路,那就是:跟着业已发展到高峰期的西方一起顺势溜向近现代文明的深渊。
这个过程并不仅仅表现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上,而是一种世界现象,也就是由西方主导的重商主义、科学主义、民主主义和殖民主义推动下的世界潮流。这表明,即便当时的中国未曾跟进,它也成不了抵制西方的中流砥柱或挽救世界的可借用力量——它的衰败早在“西方的没落”之前已成定局。
那么,文明的分层剥落或系统没落,其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文明的继续更替或继续运行,将把人类引向何方?
而文明化的社会运动未尝不是自然人性的展开过程,文明化的社会败落未尝不是人类本身衰落过程的综合体现。
从深层看,它与东方或西方、亚洲或欧洲、某国或某人全无任何直接关系;相反的,倒是各国之间、各阶级或各社团之间、乃至各人之间的竞夺和倾轧,构成了文明发展与社会运动的表观驱动力。问题的实质在于,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着生物种系和灵长人类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内部竞存?再深问一层,究竟是什么“道法”缔造了人类本身及其人世文明,且毫不怜惜地偏要将他们导向“追求发展与进步”的灯蛾之火?
总之,斯宾格勒丝毫也没有看出来“西方的没落”之根本原因。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就在他身边不远处,达尔文推出“进化论”、尼采呼唤“超人”、马克思号召“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爱因斯坦也祭起了足以调动核能与微观物理效能的科学“相对论”、等等,这一切正标志着一场更激烈的“进步主义”思潮和更危险的“文明进化”浪潮行将席卷全球。而“进步”缔造“衰落”,犹如“增长”促成“衰老”一样,这等昭彰的启示,何需那般花哨的笔墨再去作表面上的涂抹?
实话说,我原本著书立说,还没有打算与斯宾格勒对话,而是一心谋求拆解东方思想史与西方哲学史所遗留下来的最根本的疑难问题,也就是说,我更有兴趣去研究人类本性的终极源头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归宿。然而,过后回头看,却发现它能以最具有针对性的锐力直接回应“文明的进步与衰落”之课题,也就是与斯宾格勒在不同视角上面临了同一个话题。
故而才有了这类文章的汇编和这个书名的对应。